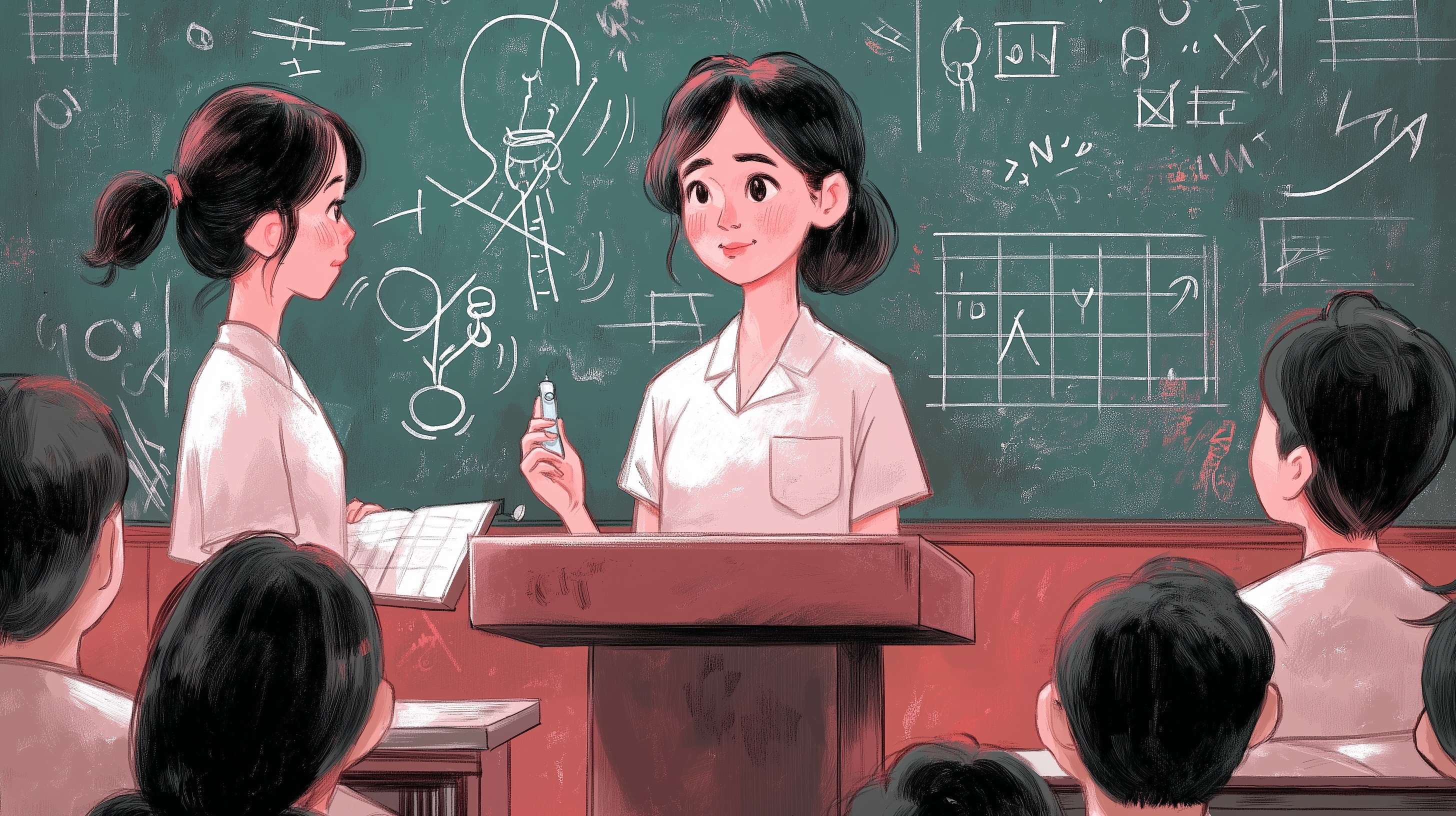
回乡以后的生活,简单到了极致。在家里的时光,闲散不已,吃吃、喝喝、睡睡、玩玩,一天大半的时光行将散去。但你又不觉得这是浪费,让人可惜。虽然在北京的生活中,时不时地我也会偶尔来上这么一遭,把一日过成如此,但它们的色彩还真的截然不同。在北京过上这么一日,总得用好几天去消化一下,这种犹如“暴殄天物”一般的浪费行为背后所积攒的自愧之意。
长假里的第二件相对高频的事情,自然是出门儿聚会。这些年里,聚会的频次实际上低了许多。还记得刚工作后的早些年里,高中同学聚会得分好几波,初中同学聚会也得来上一趟,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友、损友的单约,以及某一些说不上缘由的临时相聚。总之,春节的假日里,至少三五次聚会总是得有的。
聚会的起头,总得需要一个关键性的攒局之人。这个人得有一些汇聚众人的能量,还得有相对强的主动意愿才行。我自己底色里是个极懒的人,我并不愿意干张罗的事儿,但喜欢凑被张罗起来的热闹。所以,如果你约我一起耍,我大概率不会拒绝,但你需要我张罗点儿啥事儿,得是我最喜欢的人才行。
我仔细盘算了一下,好像过往的许多年的聚会里,我总会不自觉地承担起攒局的角色。归根到底大家都是如我一般的极懒之人,聚会这件事儿,但凡规模稍大一点,乐趣就容易被细碎的麻烦事儿抵消掉,其中沟通协调所有人的时间最费神。所以,我发现我们都一样,既想年年都聚一聚,又觉得自己起头这件事儿很麻烦。最好的方式就是,某一个小群体里的聚会,大家每一年轮班张罗,体验感和参与感可俱佳。
过去的这几年里,我张罗或参与的聚会,比起以往而言,算不得多,也是因为很多年年聚会的小团体,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状况出现,本来就四五个人,接连几次都聚不起来之后,我也就慢慢地懒得再去张罗了。聚会这件事儿也得需要正反馈的激励,尤其对于主张聚会的那个人。
今儿聚会的老同学小团体,则是个例外,我常常不用挑头只需要参与即可。尽管中间因为疫情的阻滞和各自家庭的组建,几年里也没有完全聚起来,但因为大家彼此都是好友关系,私底下也没失了联络,“组织”内部三两成群的小聚,也从没断过。所以,当我们的“主事人”从国外归来的时候,但凡在太原的同志们,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,一定会出现。
当然,今天的聚会组织之前,我们还是灵机一动,邀请了之前跟我们玩儿得好的老师们,看看能不能来参与上一番,于是,就有了今天这个“两老师”与“四学生”的难得一遇的小聚会。
说起来,我们跟高中的这两位老师的上一次见面,已经是 15 年前的事情了。老师们的身上有了一些岁月的痕迹,“杨化”说她现在眼花得不行,“峰丹”的头上也多了许多的白发。但他们俩的笑容、语气之间,却好像还是过去校园里那般平易近人又英姿飒爽的模样。
我们四个人这些年里也时不时地见面,我们自觉自己与他人都发生了诸般变化,可当我们四个跟两位老师坐在一起的时候,有那么一刹那,顿觉我们又回到了高中的教室里,除了发福之外,我们好像也还是当年那般青涩的模样。
那一刻,我竟然有些动容。这毕业后十七年的时间里,我们各自都经历了太多不一样的生活,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之中。每个人身上的肉都不是白长的,白头发也不是白冒的,脸上起的褶皱也不是白来的,它们是岁月见证之后的证明。但我们的人格底色终究还是没有变,只是这份“不变”可能只有在这样特定的场合里才能真实显现。
老师与学生,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的关系组合。他们既像是亲子关系,又像是朋友关系。我们在彼此心目当中的位置,在很微妙的变化之间游离,但终归是在一种亲近的范围里。你在外面如何如何的装扮或演绎自己,在老师的面前,你不用装,也装不得,唯一的法子就是卸掉所有的伪装,只保留最纯粹的样子。而这样的场景实在是太难得。
相对论说,只要速度足够接近光速,我们就有可能让时光倒流。今天,我们没有能够追上光的速度,但显然,时间在这张方桌旁逆流回了当年那段青葱的时空里。
一切都变了,一切又都没变。

发表回复
要发表评论,您必须先登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