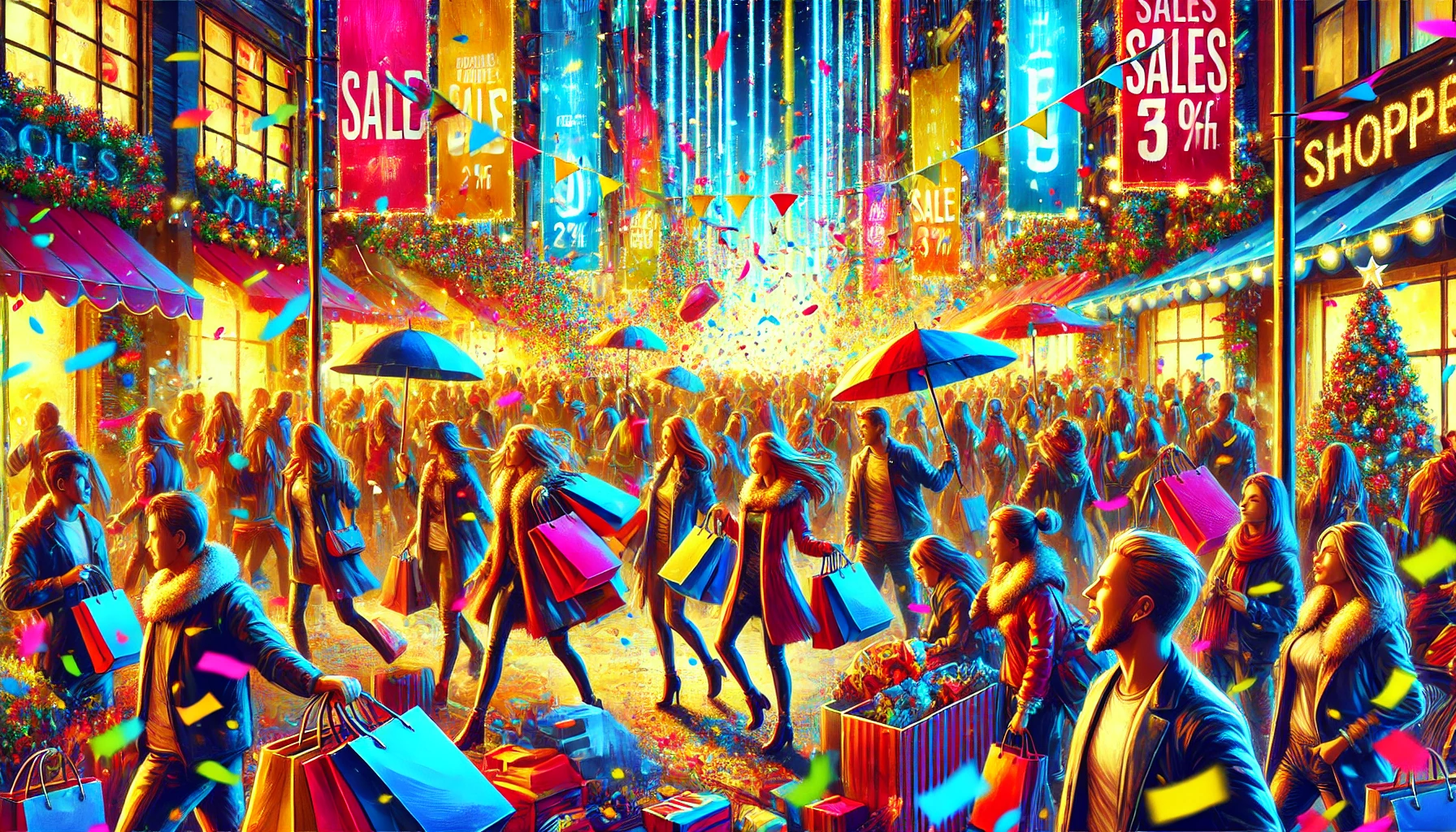
或许是因为最近在减肥的缘故,味蕾的满足受控之下,总是有一些欲望需要得到满足。于是,口腹之欲,转变成了某种购物的欲望,在这个刚刚结束的双十一的“征程”里,献祭出了既往许多年以来,最大的几笔花销。除了一些常备的日用品的“囤积”之外,还有几个金额不算小的“大件”。
本着理性至上的原则,在这几个“大件”的抉择上,实际上自己是下了一些“工夫”的。前前后后,我在其功能性和必要性上,转圜过无数次弯。其实现在看来,既然能让自己纠结无数遍,总归是说明了一些内在的不笃定的——也可以说,其们的非必要性是突出的。但是最后落单的结果,还是佐证了那个亘古不变的道理:决策的一瞬间,只需要冲动之下的感性,任何理性都得靠边站。
然而,决策层面在理性上的不确定,也是买完之后,没有获得更大的“爽感”体验的本质原因。当然,这多少是在自己预期范围里的事情。随着年龄递增,物质所能带来的“丰沛感”和满足感,实际上越来越难以获得有效的提升,它越来越接近那个“阈值”,却始终突破不了。当然,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,便是目前还没有更大的财力,去触碰那些更加贵重的东西。或许商品价值的提升,能让这个满足感的阈值再上一个台阶,也说不定。而另一方面,或许购物这个欲念燃起的原点,本就没有那么炽烈,所以,最后获得的体感上,也只能是 just so-so。
在买东西这件事情上,我几乎没有过所谓的后悔体验,即便既往的购物经历里,“踩雷”的事情也时常遇到,商品到手试用体验之后,不达预期的情况也比比皆是。但这一回,我其实很多次“闪回”那些关于“撤单”的动念和思考。它们源自于我对于新增一个物品,对当下所处的生活环境的侵入与改变的担忧。我时常已经习惯于,只增加自己高频场景里使用的物品,比如书,比如一些文创手办,比如常用的日用品。甚至于衣服与鞋子,我现在也基本控制在只在必需的时刻“出手”。
压缩物欲的本身,来自于对于“冗余”的控制不能,这是我一两年之前,突然意识到的一个问题。因为我发现,即便同一个季节,我有十身衣服,我最长穿的不超过三身。剩下的那些,如何从箱子里拿出来,过季之后就会怎样回到箱子里去。我不禁在反思,它们之于我的价值,究竟是什么?同理,这种现象也发生在生活里的其他角落里。但凡收拾上一回,扔掉的总是更大多数。从那时起,新增物品这一件事情,会让我产生一种额外的焦虑,就是如果这个东西,我用不上或者不常用或者不喜欢,那我购买它的意义是什么?
我能得出的结论竟然是,为社会的价值流通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毕竟,一件物品从成交到妥投,商家能赚 15%,平台或许可以挣 10%,快递小哥可以挣 2 块钱……我的一单虽然不起眼,但创造的社会价值,却是多样的。当然,你也可以理解为,这是一种自我 PUA 的劝慰,因为它可能给很多人创造了价值,却独独给自己创造的是负担,更要命的是,它是我花钱买的。
所以,购得新物的新奇体验感,从那一个时期开始,就已经在与“冗余”的焦虑感做减法和抵消了。这种感受的背后,让我意识到了另一句话的正确性:任何一个决策的背后都是有成本的。购物本身的成本,也不只是在时间与金钱的消费上,还在于使用价值的打折,以及精神能量的损耗。
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父母随便给我们买点小玩具、小零食,就能让我们快乐一整天的小时候了。当我为了平台的各种满减折扣而凑单、算计,从而开始堆叠更多的无效“冗余”的时候,购物的乐趣就已经要被消耗殆尽了。

发表回复
要发表评论,您必须先登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