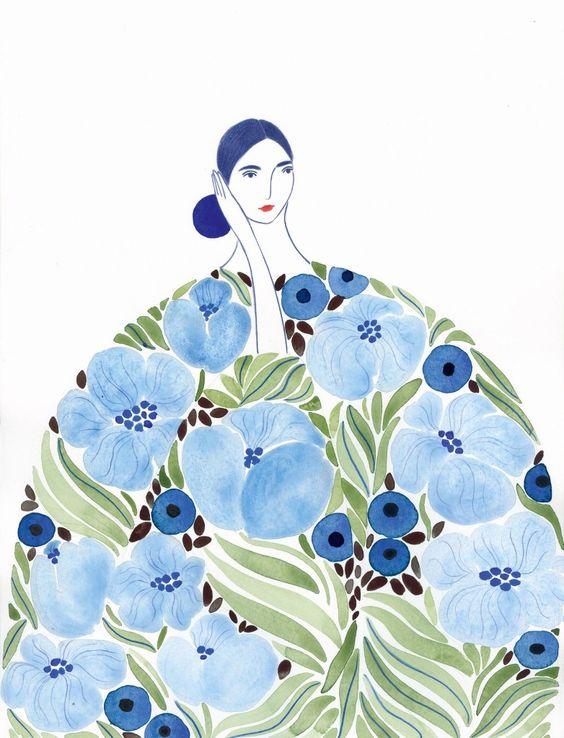
早上打车前往火车站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昨天给自己留的这个作业,该写些什么。猛然间觉得能写的东西非常多,但却一下子整理不出来任何一点脉络。
相比于再多写一些自己的感受,我可能更倾向于叙述一些所见所闻,把我自己觉得值得记录的人与事记录下来,于是,便有了这一篇文字。
病房的小格局里,只有小的故事,但小的故事里,总多人间百态。
山西省人民医院最近在各处装修,我妈所在的病区,在入院之前刚刚装修完不久,而她所在的这间病房,是这一层病区最后打开入住的一间房,但它距离打开病区的第一间病房,不过相隔一两天。
老妈是门诊当天办的入院,这不禁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:果然,小地方就是没有医疗挤兑,这种感觉真不错。但我还是低估了省级三甲医院明星科室的“魅力”,从我们入院开始,就不停听到医生、护士们的“小道消息”,说病床太紧张之类的话。慢慢地,事实证明,我们入院纯属机会巧,如果按照这周的态势,大概率得往后排队。所以,医疗挤兑,在哪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,尤其是省会城市。
我妈妈的这间病房,是这个病区唯二的六人间,大概也是整层最热闹的一间病房。周三入院的当天,病房刚打开,六张床就已经占了五张,最后一张,挤在门口处的最逼仄的那张,也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占上了。
这个科室的病人,以中老年人居多,绝大多数都是拖到不能拖的程度,不得已才来开这个刀。这间病房里,六个患者,有五个都在我妈的年龄之上,只有一个 30 岁的小姑娘。所以,只有小姑娘一个人是她妈妈陪床,剩余的五个阿姨,基本上都是儿子或闺女来。
七号床的阿姨是第一个住院的。阿姨是交城人,据说已经七十岁的年纪,但气质却像是刚过六十岁的模样。能看出来是一个衣着打扮都很讲究的人,性格也很温和,说话不紧不慢。原来是做什么的,我没太关注,只记得她是从体制内退休。
我妈是六号床,是跟七号床挨着的邻居,所以她俩平时交流比较多。听说,她有一儿一女,但全程却是女儿一人陪护到出院。女儿四十二三岁,跟阿姨的气质很像,如果不是说她四十多岁的话,我觉得至多跟我是同龄的模样。很巧的是,她也在某保险公司上班,只不过是内勤培训的岗位。尽管如此,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于业务层面的交集。同行遇到同行,有时候是蛮尴尬的事情。
当有一天,我问起我妈,听说阿姨有个儿子,但为什么没见儿子来?我妈说,她有一天无意间阿姨女儿在跟她弟弟打视频,听上去对方说话不太利索,言语之间便猜测可能她这个小儿子有些什么疾病在身。听到这里,我有点理解了这个阿姨为什么经常跟我妈夸赞自己的姑娘,说姑娘既管她这又管她那。可能在她们的家里,姑娘才是那根支撑家庭屹立不倒的“顶梁柱”吧。
五号床的妹妹,是跟我妈同时办理住院的病友。我没有询问过她家是哪里人,但她们的方言口音却是我最听不懂的,尤其是她妈妈,每次跟我们说几句话,我总得反应上半晌才能大概猜出来她说了啥。
我是一直都认为她俩是母女的关系,但我妈说,她刚开始总觉得她俩是姐妹。的确,经我妈这么一描述,如果说她俩是姐妹的话,倒也不为过。后来她知道她俩是母女的时候,还吃了一惊,这才了解到,姑娘的妈妈在 18 岁的时候就生下了她。而我听到这里,也惊奇地瞪圆了眼,连忙问我妈:确定这没犯法?
她俩是整个病房里,唯一一组“反着来”的病患与家属,但能看出来,妈妈不是个能娴熟照顾人的人,很多事情并不显得周到,还得病床上的女儿不停提醒才能做到位。术后最怕的是晕倒和跌跤,但这种风险偏偏只发生在了年龄最小的病患身上,不免让人有些唏嘘。
医院里在排号时也有讲究,比如床号在编号时跳过了所有的数字 4,所以,这间病房里,下一个床位是三号床。三号床的阿姨,从面相上看我本以为是年龄最大的一个,但看到她的床头牌的时候,才发现,她刚 68 岁。
有时候我觉得还挺神奇的,我们往往通过面相来判断一个人的年龄,每一个岁数有每一个岁数应该有的样子,而当一个人的面相与真实的岁数形成反差的时候,我们就会吃惊或感慨,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。但往往,我们的结论是,如果面相比时机年龄大,那大概率这个人这一辈子过得比较劳累,也比较苦,反之则家庭和睦幸福,感情顺遂。当然,这都是刨除疾病因素以外的判断。
三号床的阿姨有儿有女,但每天固定会来的,是她的儿子。阿姨是同时跟我们一起入院的,可直到我妈出院,阿姨的手术都还没有开始做。入院的时候,因为不太熟,我们也不好过问。直到出院的那一天,我们才知道,可能是因为阿姨的病情相对复杂,需要排队做核磁的检查,才一直“耽误”至今。
我想,每个家庭总有它的故事。这个家庭,我并不知道他们真实发生了什么,只是在听他们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才知道,她的这个儿子,今年 44 岁,有三个孩子,离了婚,前妻把三个孩子都抛下了,回了甘肃。儿子在太原打工,三个孙子孙女,都只能由他们的奶奶——三号床的阿姨来照顾。阿姨 68 岁了,现在还在打工养活这三个孙子。
我妈说,是不是遇上“婚骗”了?我却不知道,一个“婚骗”为什么可以生完三个孩子才走?
二号床的阿姨在我看来,甚至是这所有阿姨里,最让人觉得幸福的,当然,这个阿姨的确也是所有人里实际年龄最大的一个。为什么说让人觉得幸福?因为阿姨有五个闺女。这几日里,大家排好班次轮番上阵,每一个闺女的性格都不一样,但一样的是,大家的照顾都肉眼可见的无微不至。
我跟我妈说,这让我看到了她们姊妹几个照顾我姥姥的场景。我妈却说,有个闺女真挺好的。
从现实角度来说,我很认同于老妈的这番话,真到照顾病人的层面上,先不说方便与否,但女孩照顾得的确更加细心和贴心。但老一辈人的眼里,却似乎总对女儿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,也会更沉溺于「天经地义」「理所当然」的那一套老派的“厌女”情结当中。即便是在这个和和气气的一大家子里,我依然总会有一种与我自己价值相错位的违和感。
这个社会的男女地位也许已经趋于平等,但人们世俗观念里的平等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。
一号床在这几天里换过“主人”,第二天就入院的那一位阿姨,一直在同时做肺部的理疗,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患者,所以在第三天的时候就转到了其他病房里重点观察,我们与她也失了交集。但病床连半天也没得空闲,便立刻又住进来了一位阿姨。
这个阿姨跟我们算半个老乡,是侯马人。侯马虽然隶属于临汾市,却跟我的老家,运城市的稷山县毗邻,所以,我们坐高铁往往会选择坐到侯马再打“拼车”回去。两地因为紧挨着,所以方言也很相像。阿姨是个挺 E 的人,虽然看上去有股文质彬彬的感觉,但却是最快融入到这个“大家庭”的人。她只有个独生子,据说三十岁左右,所以全程的陪护,也是她儿子随时在侧。
我在她儿子身上总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,不知是样貌的缘故,还是表现出来的性格的原因,他总让我觉得特别像是我认识的几个朋友的结合体。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,倒蛮有意思。
我妈说,这个男孩当初也在北京,是后来他妈妈“逼”着他回到了太原来。我没听到这中间的故事,但类似的故事,数度发生在我的许多朋友身上。以前公司的 HR 当年想让我调回太原大区的时候,就跟我提过,说我们山西人都恋家,最后大概率还都得回来。这么多年过去,我的确也越来越相信她说的这番话,只是,我自己可能自由惯了,真让我权衡利弊,我可能还是更愿意在外面“漂”着。
病房是个临时组建起来的“小团体”,大家与其说是真的对脾气,不如说是因为住院的磨人与无聊之下,自己找乐子的一种方式。但就像大家分开的时候,都心照不宣地礼貌告别,也没有任何人主动提及一句留下谁的联系方式的话一样,这一切都是临时的一场戏,表演完毕,谢幕离场就好。
而我觉得有些惋惜的是,我更想要看看那些表象之下的故事究竟是什么。只不过,时机总不显得那么对,而我们也最终各自离开。大家都对自己的生活习以为常,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需要分享的故事。而我觉得,每一段人生故事,都有其背后的意义在,它们需要被看见,也需要被讲出来。

发表回复
要发表评论,您必须先登录。